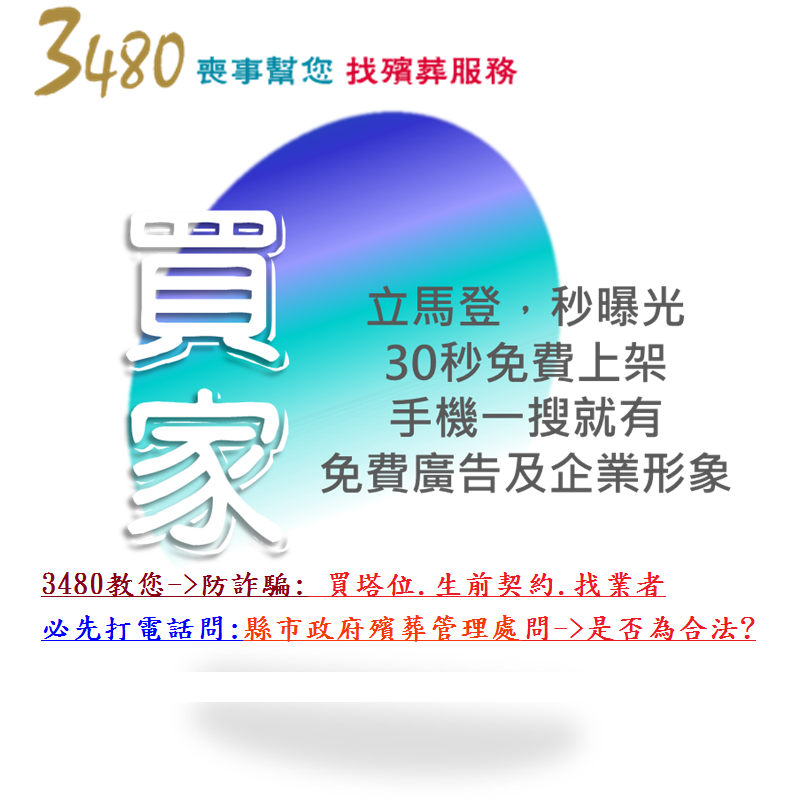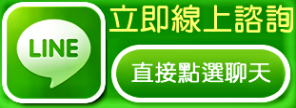編按:卡力伯‧懷爾德是美國殯葬事業第6代傳人,入行17年,參與近4千場葬禮。在看盡善終與非善終、人性美好與不堪後,寫下一個個令人動容的人生告別式,同時分享最真摯坦率的生死體悟。
面對邪惡的過程中,有個想法在我心中逐漸成形,那就是我要幫助世人進入天堂。我在葬儀社的工作經驗,例如無法解釋又令人心痛的幼兒遺體,不但鞏固了我的死亡負面論述,也加深了我對天堂的信念。因為,如果這世界如此悲傷、無常、令人心痛,我只能盡力幫助大家逃離墮落的地球,進入天堂。只要相信有天堂,處理遺體之類的工作就會顯得微不足道,因為眼下的人生遠遠比不上死後的人生。
我高中暑假都忙著深夜接遺體、除草、洗車、在喪禮上幫忙跟洗殮房。洗殮房就跟洗公共廁所差不多。有很多奇怪的污漬跟飛濺的痕跡,要刷洗很久才清得乾淨。對一個想要散播上帝之愛、幫助世人上天堂的高中生來說,這些工作實在沒什麼啟發性。
我在喪禮上幫忙的時候,親切的老太太們總會對我說:「你加入葬儀社一起工作真是太好了。現在我可以死得很放心,因為我知道我的後事會由懷爾德家族的人處理。」有幾位女士甚至把我拉到一旁,偷偷告訴我:「別忘了幫我刮掉臉上的毛。」我微笑以對,讓她們捏我肉特別多的臉頰,但同時我心裡的想法是:我可不想一輩子都幫帕克斯堡親切的老太太刮臉毛。我想做一番大事,冒險犯難、做可以改變世界的事,我要帶領世人上天堂,而不是忙著幫別人刮掉多餘的毛髮。這層領悟形塑了我的第二個經驗:我決定到偏遠地區當傳教士,與世人分享上帝之愛,確保他們死後都能上天堂。
於是,2000年高中一畢業就決定成為傳教士,慈愛的祖父依然在財務上支持我,因為當時的我認為,以傳教士的身分幫助世人進入天堂、遠離地獄,是我能做到的最佳善行。
為期數月的傳教士訓練轉眼就結束了,2001年初,我加入一個由12人組成的人道團隊,轉了幾趟單引擎螺旋槳飛機,前往馬達加斯加沿海叢林裡一個遺世獨立的地方。我加入基督教傳教團的初衷是希望能「拯救靈魂」,但是這支團隊更著重於人道工作,這個巧合很可能徹底扭轉了我的人生。
駐紮此地的兩個星期內,我們用有限的醫療設備治療了一千多人。其中一名病患永遠改變了我的人生觀。那位男性年約五旬,腹部腫脹,扭曲的表情寫滿痛苦。雖然一息尚存,但恐怕是活不久了,因為他無法接受現代先進醫療的救治,也沒錢看病。
我們是他僅有的醫療機會。酗酒導致的肝硬化併發腹水,使他的腹部液壓上升,十分痛苦。一心救人的兩位醫生想以放水的方式幫他減輕痛苦。我自願負責壓住病患,好讓醫生把一支大針筒戳進他的腹部,藉此放出腹部累積的液體並紓解疼痛。那位病患在針筒插入時踢腿掙扎,我全身的重量幾乎都壓在他的下肢、拚命固定他的雙腿,以免妨礙醫生工作。我很清楚我做的事無法解決任何問題。我並未拯救任何靈魂。我只是陪著他承受痛苦,而不是解決他的痛苦。陪在他身旁,是我唯一能為他做的事。這也是我們全員唯一能做的事。
醫生幫他放完水後,過了幾分鐘,他臉上的痛苦表情漸漸消失。他望著我們,用馬拉加西土語輕聲說:「Misaotra」(謝謝)。陪伴在他身旁的家人一邊撫摸他的臉一邊掉淚,因為他的痛苦總算暫時消退,某種程度而言也算恢復了意識。
對當時的我來說,死亡負面論述與隨之而來的天堂信念都讓我忽視了良善的價值。我們很容易犯這種錯。新聞天天播報悲劇:暴力、流離失所的難民、無家可歸的遊民、貧窮、戰爭造成的死傷,再加上我們個人的逆境:家庭破碎、疾病、勉強餬口度日。人很容易緊緊抓住這些悲劇不放。恐懼占據我們的心思,導致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,老是把「地球不是我的家」掛在嘴邊。這句話有兩層涵義:一是邪惡、仇恨與不公不義,都無法代表我們想要居住的地方。二是天堂才是我們應該居住的地方,地球只是我們前往永恆的家鄉之前,必須暫時落腳的住處。把世界當成通往天堂的墊腳石,會讓我們覺得好過一點。我們想要有來世,想要另一個世界,尤其想要上天堂,所以認真耕耘地球這座花園並不容易,因為相信有天堂的言外之意,即是來世肯定是一個更好的世界,反正地球已經糟糕透頂。
但是,只要偶爾專注於當下,就會發現有些美麗的事物只可能出現在地球上。它短暫地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。它短暫地紓解了疼痛。它短暫地生出了愛。在那一個個短暫的片刻裡,我們得以瞥見地球的光輝。天堂或許燦爛耀眼,但地球其實也不差。
我千里迢迢跑到非洲,才發現或許散播上帝之愛最好的方式,並不是坐等命運降臨在我身上。我漸漸明白我的家鄉美國就有一個絕佳的機會,讓我得以在葬儀社為這個世界奉獻善行。恐懼與未知依然存在,但是我開始聽見另一種論述的聲音,那聲音輕柔地告訴我們要活在當下、活在此時此地,就在這個我出生長大的地方。因為天堂說不定就在這裡,藏在引發恐懼的悲劇背後,只是我們的雙眼被這些悲劇蒙蔽了,才看不見天堂。
一路走來,我學到了猶太人的「tikkun olam」觀念,意思是「療癒世界」,透過在痛苦中的陪伴來實現。這個觀念可以簡單解釋為「我在這裡陪你,我愛你」,光「在場」這個簡單動作便可達成。身為禮儀師,這個觀念成了我奮鬥的口號。
瑞秋.娜歐米.雷門(Rachel Naomi Remen)在接受克莉絲塔.提皮特(Krista Tippett)訪問時,說「tikkun olam」是「一種集體任務。牽涉到每一個曾經出生的人、目前活著的人、即將出生的人。我們都是療癒世界的人──不是靠大幅改變現況來療癒世界。重點在於那個感動你的世界。」
小小的「tikkun olam」其實無所不在,天天都在發生:
母親安慰孩子,就是在療癒世界。
專心聆聽另一個人說話,就是在療癒世界。
護士為年邁體衰的病患沐浴,就是在療癒世界。
老師為學生全心奉獻,就是在療癒世界。
鉛管工人讓房子的水管維持通暢,就是在療癒世界。
一位禮儀師發現,經營家族事業也能夠療癒世界。
雖然「在場陪伴」不一定能改變任何人、改變任何文化,也沒有移山之力,卻能夠發揮療癒作用,尤其是療癒我們自己。我花了不少時間才知道:我能以禮儀師的角色做什麼事。領悟之後,這份工作忽然變得無比重要、舍我其誰。
陪伴,有其職責與功用。陪伴能發揮的作用就是接納當下,接納這世界,接納地球。從某個角度來說,有點類似助產士的功能:等待、傾聽,並在新生命降臨之際,發揮穩定與指導的作用。不一定非得是大型工程、計畫或行動不可。有時候,改變世界的確需要大規模的行動,但大部分的時候,只要願意陪伴、傾聽和釋出善意,就足以改變世界。我本身相信,改變始於接納這世界,全心全意活在當下,而不是冀望來生與下輩子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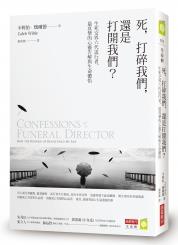




 卡利伯.懷爾德(Caleb Wilde)
卡利伯.懷爾德(Caleb Wilde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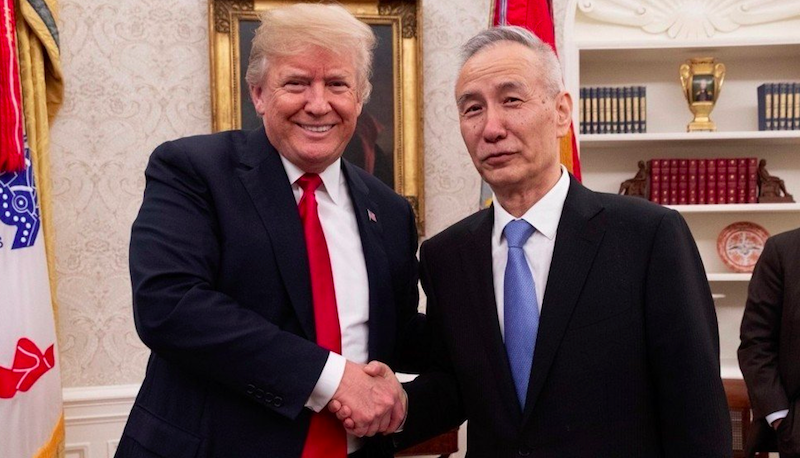 川普:中國會購買我們偉大的農產品!中美貿易戰談了半天,關鍵問題根本沒討論
川普:中國會購買我們偉大的農產品!中美貿易戰談了半天,關鍵問題根本沒討論  被美國踢出環太聯合軍演 中國反嗆:沒有建設性的決定
被美國踢出環太聯合軍演 中國反嗆:沒有建設性的決定  體驗初夏輕奢華的浪漫,來去澎湖搭遊艇賞花火
體驗初夏輕奢華的浪漫,來去澎湖搭遊艇賞花火  《達文西密碼》作者:未來世界將因AI與科學,發展出全新物種
《達文西密碼》作者:未來世界將因AI與科學,發展出全新物種  在家就能工作,卻堅持員工到公司...日本最狂企業家揭露:你會覺得忙,不是因為工作太多
在家就能工作,卻堅持員工到公司...日本最狂企業家揭露:你會覺得忙,不是因為工作太多  成大航太博士35歲在越南蓋房子創業
成大航太博士35歲在越南蓋房子創業 誰殺了牛仔褲?
誰殺了牛仔褲? 不到0.1秒的過程,你交出了什麼?
不到0.1秒的過程,你交出了什麼? 行銷人必學!以簡化繁新觀念
行銷人必學!以簡化繁新觀念![[職場講座]27歲當上CEO,她如何做到?](https://admsmaterial.businessweekly.com.tw/1c9cd731-87e8-48a3-ba6e-078dec2aeb1a/custom/%E5%95%86%E5%91%A8com_576x325.jpg) [職場講座]27歲當上CEO,她如何做到?
[職場講座]27歲當上CEO,她如何做到? 生命靈數艾莉絲Iris老師為您解析職場運勢
生命靈數艾莉絲Iris老師為您解析職場運勢 花5分鐘說不清楚的,不如畫一張圖
花5分鐘說不清楚的,不如畫一張圖 會員獨享,商周知識庫7天免費
會員獨享,商周知識庫7天免費